——我眼中的戈迪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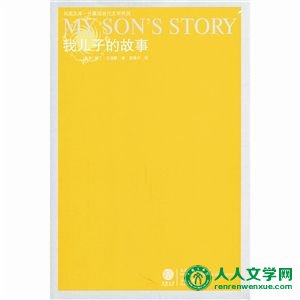 戈迪默的作品《我儿子的故事》、《爱的讲述》。
戈迪默的作品《我儿子的故事》、《爱的讲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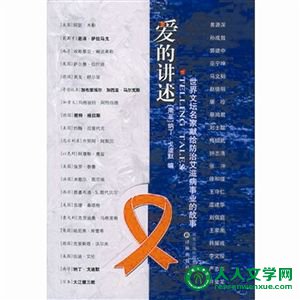
 南非著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南非著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戈迪默的作品《新生》
戈迪默的作品《新生》当地时间2014年7月13日,南非著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安然逝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祖马在哀悼信中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祖马的话其实也表达了全世界无数人对戈迪默的哀悼、怀念和崇敬之情。
戈迪默走了,这个对我来说很特殊的人走了,我禁不住要说一说她,说一说她那些独具特色的作品。二十二年前,我曾经花费一年多时间翻译她的小说《我儿子的故事》。当时我几乎每天都在感受她的思想与情感,几乎每天都在与她笔下的人物共悲欢,那段经历已成为我生命历史的一部分。如今戈迪默走了,叫我怎能不感慨万分!
1991年戈迪默因其“壮丽如史诗的创作对人类的贡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南非作家。戈迪默一生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和200多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它们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戈迪默的主要作品有《说谎的日子》(1953)、《陌生人的世界》(1958)、《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1966)、《尊贵的客人》(1971)、《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博格的女儿》(1979)、《七月的人民》(1981)、《士兵的拥抱》(1983)、《大自然的游戏》(1987)、《根本的姿态》(1988)和《我儿子的故事》(1990)等。
戈迪默终生关心人类的解放,历来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因此她的《陌生人的世界》、《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和《博格的女儿》在南非曾分别被禁达10年、12年和4个月。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英国)、马拉巴特奖(意大利)、奈丽·萨克斯奖(德国)等不同,作品三度被禁是戈迪默的另一种荣耀。戈迪默身为白人,却始终在为受凌辱的黑人鸣不平,她的作品在南非被禁实在不足为怪,她被誉为“南非的良心”也绝非偶然。
戈迪默是犹太人后裔,父亲是自幼逃离立陶宛的犹太人,母亲则是来自伦敦的犹太女子。她1923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从小目睹过很多没有妻室、没有儿女的黑人矿工饱受奴役的遭遇。另外她从小喜欢读书,曾深受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等作品的影响。因此戈迪默成年后同情黑人,以作品描写和抨击种族歧视制度的邪恶,可谓顺理成章。
1
她的小说中,既有黑人的毁灭也有白人的毁灭
儿时的经历与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儿时所目睹的众多伤害(主要是黑人的苦难),免不了要在戈迪默的作品中留下印记。戈迪默18岁时写过一篇《要做的善事》,讲的是一个孩子与一只鸽子的故事:那只鸽子被人用弹弓打中了,它受伤坠地后奄奄一息,痛苦不堪。孩子愿把鸽子放进笼里饲养以恢复元气了,可是没有希望。于是孩子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看着鸽子疼痛而死,要么把它杀死。最后小姑娘脱下鞋子,朝鸽子的脑袋重重一击……这样一个故事虽然简单,其对痛苦的表现却富有力度,显示了青年戈迪默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作家的潜质。
读戈迪默的作品,你会想起《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托夫人,或宣布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他们三人都有博大的胸襟,都超越了狭隘的种族偏见,都深刻地理解了自由:在别人不自由的情形下,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在有奴役存在的国度,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不堪种族歧视之苦,南非黑人的反抗愈演愈烈,致使白人也同样不得安宁。戈迪默非常明白,虽然白人当局可以杀戮,可杀戮只会造成仇恨,不能带来和平与安宁。她用小说揭示南非社会的病症,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南非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
必须指出的是,戈迪默所同情的不仅仅是黑人,她既描写了种族歧视给黑人造成的深重灾难,也表现了由此对白人自身造成的戕害。比如在《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戈迪默刻画了在白人统治下一个白人的悲剧:白人麦克斯反对种族歧视,他愿与黑人并肩奋斗,可是他却无法真正和黑人融为一体。他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可是在现实中却困难重重。后来他在警察的逼迫下出卖了白人、黑人同志,感到羞愧难当,最后内疚地选择了自杀。随着黑人被枪杀,白人走向自我毁灭,戈迪默同时为黑人和白人叹息。
戈迪默聚焦于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与白人的命运,其作品有浓郁的反种族主义色彩,或者说有政治特色。一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种缺憾。但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戈迪默的良知与可敬,因为当时她所处的南非的现实是:种族冲突异常激烈,社会有如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她没法回避这一现实。明知某处人群中有个炸弹却视而不见,仍然煞有介事地咏唱玫瑰与彩虹,这样的人不是虚伪矫情,就是心智有毛病。戈迪默与这类人截然不同,她选择了直面南非的现实,并希望能为改变现实尽自己的一份力。
在一个处处有压迫的充满杀机的社会,人的心灵是扭曲的。戈迪默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那种社会里,发生在我身上和我的小说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情感的扭曲。就像婴儿的脑袋卡在了产道里一样,生活在南非,你的个性和感觉时时都受到压抑。”这种扭曲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可能是毁灭性的。难怪我们在戈迪默的小说中能看到种种毁灭——既有白人毁灭黑人,也有白人毁灭白人,还有黑人毁灭黑人。戈迪默表现这一切,旨在警醒整个社会,唤起一种共存的意识。
2
她的作品有政治色彩,但并不图解政治
戈迪默的作品有政治色彩,这毋庸置疑。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戈迪默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政治鼓动家,因为她并不图解政治,她不是靠政治宣传获得认可的。早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1953)问世时,《纽约时报》就这样赞扬它:“洞悉人生,思想成熟,笔法新颖自然,独具个人风格,堪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媲美。”戈迪默不过是用文学的笔法表现了种族歧视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扭曲与极度痛苦,而且她的表达是生动而深刻的,从《我儿子的故事》和《七月的人民》等可窥一斑。
在《我儿子的故事》中,黑人革命家索尼的儿子威尔发现父亲和白种女人汉娜有奸情,感到惊讶和恶心。威尔之所以恶心,是因为他爱自己的母亲,还因为他对白人心怀怨恨。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威尔怨恨白人,另一方面他做色情梦时梦见的又偏偏全是白种女人。戈迪默通过威尔的行为突出地表现了黑人对白人既怨恨又欣羡的扭曲的病态心理,这无疑也显示了她对社会矛盾和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
戈迪默以丝丝入微的笔触刻画了威尔的诡异心态,这已是难能可贵,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她剖析了导致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她借威尔之口说:“当然如此……我在咸湿梦中梦见的尽是金发碧眼女人。这是法律的影响所致,法律决定了我们是什么,而她们——那些金发碧眼的人又是什么。结果我们这类人都成了病毒携带者,血液中有病毒,本人也许并未发病,却能把病毒传给别人……”正是这种剖析让戈迪默的作品获得了不同凡俗的广度与深度。同时戈迪默也以其作品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使命不仅仅是讲故事。
在《七月的人民》中,戈迪默设想出颇具真实性的情境,预言性地叙述了内战的恐怖。她让白人和黑人易位而处——白人当奴仆,黑人当主人——让白人亲身感受到了种族隔离的滋味。在此黑人中心主义取代了白人中心主义,其结果同样是可怕的。把白人和黑人的地位颠倒,这种构思并非空穴来风。在反对种族歧视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阻碍着南非民族的融合:其一是白人当局要维持对黑人的暴力统治,这是典型的白人中心主义;其二是有些黑人希望建立一个纯黑人的政府,这是黑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或者说是黑人中心主义。在同情和支持黑人运动的同时,戈迪默也指出了黑人运动中存在的弊端。她抛弃了白人中心主义,但并不赞同黑人中心主义。她所关心的是所有人的解放,不分种族和肤色。
3
她被誉为 “预言现实主义”
戈迪默从现实设想未来的创作手法,被评论家誉为“预言现实主义”。不过戈迪默本人对这个赞誉似乎并不太认可,她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是开现在的玩笑,看看我们正在南非干些什么事,完全有可能出现那种结果。小说写出来后的这些年,许多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预言家,而是因为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发生那样的事。” 正是对南非的社会症结的洞察与反思,让戈迪默在高度和见识上胜出很多作家一筹,因此她成了南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当年戈迪默以笔为武器挑战南非的种族主义(早在1962年时,她就为反种族歧视的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起草过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格独立、个人勇气与社会良知,其中人格独立是基础。在接受采访时,戈迪默说过:“我认为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要运用自己的洞察力——超出他人的洞察力——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不要担心你政治上的同道会怎么看你。”她还说过:“最好的写作方式就是好像你已经死了,不害怕任何人的反应,不理睬任何人的观点。”
尽管作品三度被禁,戈迪默却从未放下过她犀利的笔。她的作品在欧美各国不胫而走并为她带来一项项荣誉。1991年当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立即公开向戈迪默致贺,说这也是南非的光荣。而戈迪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只要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全白人的政府,我就不会从他们那里接受任何表扬,从前不会,将来也不会。”可喜的是,在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狱才4年的纳尔逊·曼德拉于1994年5月11日当选为南非总统,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安然去世之前,戈迪默看到了南非的正义梦想的初步实现,料想她走时是欣慰的。
出于对南非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的一片深情,戈迪默曾谢绝多个国家邀她去定居的邀请。她曾经说,虽然她反对种族主义政府,但她决不愿离开本土,因为留在南非,她可以让她的作品起些作用。假如种族歧视政策下的南非是地狱,她宁愿留在地狱,戈迪默就是这么豪气!戈迪默希望她的作品能“起些作用”,这说明她是把创作当作一项使命来完成的。希望能用自己的创作唤起黑人的信心和白人的良心。在文学之外,戈迪默以自己的行为阐释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最重要的两种个人品质:永葆人格独立,担当社会责任。
生理的戈迪默走了,精神的戈迪默还在,从现在到未来!
(作者简介: 莫雅平,诗人,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儿子的故事》译者,现居桂林。)
责任编辑:人人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