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
作者|郭勇
女人为他生下了第五个儿子。想不到,几世单传的老范家,到他这辈子,居然有了五个儿子,算是给先人长了脸。更想不到的是,老五的出世却要了女人的命。那时候他的老大才十二岁,一个挨一个的五个秃头,他有啥办法。只好忍着揪心的疼,把老五送了人。从此他开始了既当爹又当妈的艰难岁月,一门心思地拉扯四个孩子。白天挑个货郎担走村串户,换点钱米;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笨针拙线,缝缝补补。孩子有个大灾小殃的,就更要了他的命,顾了小的顾不了大的,顾了病的顾不了好的。
生产队里好多人都和他比,说别人都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他是哪个林子里飞来的鸟,一天挑个货郎担走东串西地发展资本主义。队长说,你们谁的老婆要是死了,也丢下几个小碎娃,我也不管你!再说了,把他收拾回来,大的小的一屋子,日子过不下去,你能看着叫人家的娃子们冻死饿死,还不是给生产队里添累赘?队里的人从此也就不再追究。
老大老二已到上学年龄,两个小的无人看管,家里零活没人干,念书总没有吃饭要紧,只好作罢。但他不能让孩子们成了睁眼瞎。他就一边忙着,一边抽空把自己在扫盲班识下的几百个字教给孩子们。
有人劝他找个女人。他也觉得没有女人的日子比年长。“给你们找个新妈吧?”他流着泪给老大老二说。老大老二也流着泪,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他知道孩子们心里不愿意。可他还是决定找一个。
一天他挑着担儿去叫卖。围过来几个带小孩的女人。孩子们见了货郎担,都围上前闹着要买糖吃,不论大人们怎么叱喝也不听,硬是拿着糖块不放手。这时又走过一个女人,身后跟个小女孩。小女孩见孩子们都拿了糖块不放手,便也忍不住伸手去拿。她刚一伸手,又马上在半路停住,抬头看那女人,那女人脸一沉,眼一瞪,小女孩象炮烙似地缩手,后退几步,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后来他知道了那是个后妈。他忘不了那个后妈可怕的一眼和那个缩手呆立的小女孩。
从此,他打断了给孩子们找后妈的念头。宁可自己多吃点苦,受点累,也绝不让孩子遭后娘。就这样,他和四个孩子相依为命,熬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点把孩子们养大成人。
说慢也慢,说快也快,几年之后,儿子们都齐刷刷地长大了。可他反而觉得路程更远担子更重。
父愁子妻。老大已经十八九了,没有念下个书,就在农村翻土块。要是不早点给抓将个媳妇,年龄一大,可就难了。可是,眼下这个烂包相,谁家的丫头给呢?就说有人给,娶进门你让人家姑娘住哪儿啊!娶媳妇,先得修房子。于是他把修房子的事情给儿子们说了之后,就带领他们干开了。依老大的主意,现在家里穷,先修三间,过几年好点了再修。可是他觉得还是一次性修八间。背亏累债,就打一次麻烦。他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儿子们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趁现在还能镇住他们,就下决心弄八间,到时候一人两间,谁也没的说。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儿子们齐心协力修了八间房。房子刚修好,赶上包产到户,又分了地,分了农具,一家一户可以单干了。他不知道这种政策能维持多久,但他还是觉得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就不能错过,谁知道啥时候又集体呢。他就带领老三老四守家种地,养羊养驴,务侍家庭副业。打发老大老二出去打工。一家子五条劳力,没有吃闲饭的,呼啦啦,两三年,日子就有了起色。修房子累的债也差不多还上,家里还添置了一些像模像样的家具。孩子们雄心勃勃地要在明后年买辆小四轮。
这时候的老大已经二十三,老二二十一,老三十八,老四十五了。前面的三个没有让念书,是他最大的内疚。一同岁的娃娃,谁家的都多多少少上过几天学,就他的不知道学校门朝哪面开。不过,他稍感欣慰的是,他把自己拾来的那几百个字都教给了孩子们,加上孩子们的悟性,现在还算是都勉勉强强睁开了个眼睛,也还能读个报,写个信啥的。他想叫老四去上学,总得供出一个吃皇粮的吧,家里出个人,不说光宗耀祖了,也是家门的个依靠。老四在学习上很上心,说不定还真能有个出息。他征求了大伙的意见,三个哥哥都同意。老四也表了态,一定好好学习,将来为范家争光。他为了让老大老二老三心里没有疙瘩,就把家务和庄稼活全揽了,说,你们哥儿三个都出去吧,我还不老,有小四子给我搭个手,家里的这点活我能行。你妈死得早,我把你们拉扯到今天,都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俗话说,父愁子妻,子愁父葬,我现在最愁的就是你们的婆姨。现在给你们个任务,谁的婆姨谁挣去。小四子的学费和家里的开销由我管。
说是这样说,第三年老大娶媳妇,还是统筹兼顾,除了拿的彩礼和婚事上的花销是老大挣的,家里摆席用的猪啊,羊啊,鸡啊,粮食啊,菜蔬啊什么的,全是自家产的。添置家具,布置新房的花销,是老二和老三出的。大媳妇就这样红红火火地娶进了门。十几年的光棍之家第一次有了女人。
有了女人,原来的习惯就被打乱了。总是有点不怎么习惯,不怎么适应。不管怎么不习惯,不适应,都得慢慢的适应、慢慢地习惯。打乱了格局的新家庭得磨合一段时间才行。媳妇是人家的人,一下子到一个新的环境,本来就不怎么适应,谁都小心翼翼,极力地迁就女人,尽量适应新格局。三个儿子一天嫂子长嫂子短地叫得欢,他叫不出口媳妇的名字,就叫老大家。一开始媳妇不习惯,说,爹,我不是有名字吗,你咋老大家,老大家的,难听死了。他说,那个啥,我还是这样叫顺口。第二天,老大说,爹,你还是叫她名字吧,不要为这么点小事那个啥了。他没有办法,就别别扭扭地叫了几回刘爱琴。后来还是觉得别扭,就不叫了,有时候“哎”一下,有时候就啥也不叫,白搭话。总之吧,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有了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而大家又都自觉自愿地适应着。
那一天,老大陪媳妇站对月去了。他想出去边散心地拾点柴火。不经意间,他看见老大新房门上吊了一把明晃晃的新锁。他的心咯噔了一下,有一股被冷落的感觉生出来。进门还没有几天,就?这个院里都是自家人,她锁谁呢!他不想出去转了,怏怏地折回自己的屋里,躺在炕上想心事。这是一个信号,她把这个原本完整的家划了一道缝,最终是想要隔离出去。尽管他很失落,也很丧气,但转而一想,分家是迟早的事情,为什么一定等到矛盾出来再分呢?春节一过,儿子们都要出门打工,小四子也开了学,家里只剩下公公媳妇,咋相交呢?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家里能没有个磕磕碰碰,等到出来矛盾就不好了。还不如趁早好好道道地把家分了,谁的日子谁过去,免得日后老子不是老子,儿子不是儿子的。他这样一想,心里就又好受了些。可是又一想,媳妇才来一个月,就分家,别人咋看呢?是说我不好,容不下媳妇,还是说媳妇不好,刚来就闹出来啥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嘛,新婚房里也或许有啥不愿让人知道的,锁一下,也能理解。儿子结婚刚满一个月,老子就提出分家,这不是往出赶吗?他就又把分家的念头暂时搁下了。
媳妇站对月回来,就到了年跟前,老二、老三也都回来了,小四也放了寒假。大家兴致勃勃,想高高兴兴过个年。儿子们扫房的扫房,办年货的办年货。小四把所有的水缸、水盆、水桶都挑满了,在院子里绷了几道铁丝,说要用嫂子的陪嫁洗衣机把身上穿的,炕上铺的盖的,彻彻底底洗一遍,干干净净过个年。小四把这些都弄好了,去叫嫂子。嫂子,今天我和你洗东西。嫂子说,你一个人先洗,我还忙着呢。小四说,也行。那我和你把洗衣机抬到院子里,我洗就我洗。嫂子一声没吭,沉了半天说,那是陪房货,你给人家弄坏了。说完,一甩手掀起门帘进了里屋,把小四凉在那儿。他看见了,也听到了。就说,小四,去给驴添点草去,把猪也喂了。小四噘着嘴去给驴添草。这又是一个信号,她的东西别人不能用。分家!就在这一刹那,他下定了决心。
正月初六老大两口子拜完了年节回来,他召开了家庭会议。说,孩子们啊,今天爹有几句话想说说。来,我们爷父们先端个酒,老大,给你媳妇也斟上。
爹,有啥你就说,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的。老二说。
他端起酒杯,慢慢在地上奠了一缕,说,先给你们的妈奠上一杯。老婆子,你把我扔下十几年了。说到这儿他声音有点哽咽,鼻子酸酸的,眼睛模糊了一下,又极力地忍住了。没有你,我照样也过来了,孩子们都争气,也没有学坏。今年老大娶了媳妇,明后年咱就有孙子了,好日子才开始呢,你要地下有知,就好好保佑他们吧!
爹,今天过年呢,还是高兴些吧,我们还都等着听你说事情呢。媳妇说。
就是,妈都死了十几年了,我们也没有啥印象了,小四和老三都不知道妈是个啥样儿呢。老大顺着媳妇的话说。
好,不说这些了。孩子们,俗话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个家能到今天,全是你们大哥帮的我。现在你们都自己能够着饭碗子了,就再不要拖累你大哥了。现在他也娶了媳妇,他们的日子就由他们自己过吧。
爹!你啥意思?嫂子刚进门,你就,不怕人家笑话?老三说。
老大说,爹,这不行,我咋能刚娶了婆姨就分家呢,这么一大家子,我不管谁管,我是老大,我有这个义务。
孩子们哪,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哥儿们分家是迟早的事情,迟分不如早分。我注意已定,你们说啥也没有用!要说分,也没有啥分的,就是个形式,就是单另搭个锅罢了。老大,你们两口子就住你们现在的两间,你们屋里的东西就给你们。土地按哥儿四个平均分,一人4亩,你媳妇没地,就把我去年开的六亩滩旱地给你们,尽管缺水,每年还是能收几个,斤里不添两里添呢。牲口、农具就不分了,我给你们经管着,谁使谁就使。锅锅碗碗这些应手使的器具,你媳妇看,拿个啥就拿个啥。分是分了,以后哥儿们还是哥儿们,互相帮衬着,不要让旁人看了笑话。来,我们爷父们干了这杯!
前有车,后有辙。几年之后,老二、老三娶了媳妇,都先后分出去了。小四考了个中专,毕业分到玉门油田上去了。
他成了一个人。
起先,儿子们还都住在一个院里,虽说他一个人住,倒也并不寂寞。一天又是孙子,又是牲口,不是给这家喂个猪,就是给那家拔个草。吃饭时几个孙子都来叫爷爷,或是媳妇、儿子端过来。忙是忙,倒还实在。隔三岔五,小四还寄点钱来。吃个药,抽个烟,喝个茶的,手头也不是太紧。
就这样过了几年,院子里的矛盾出来了。先是三个媳妇各不相让,不是你家的鸡蛋丢了,就是她的娃娃被你的打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弄得比猪骂狗,捎讽带刺。男人们禁不住枕头风吹,兄弟之间也就慢慢有了隔阂。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老大批了新宅基地,拆了旧房,搬出去住了,接着是老二,也把自己的两间老屋拆了,外面修了新房。老三媳妇也不拉下,极力撺掇男人搬出去住。老三起先不肯,说我们都走了,爹一个人咋住。婆姨说,爹又不是我们一家的爹,他们走了,凭啥要我们管。你看这个院子拆成这个破烂相,住在这里你不丢人我还嫌寒碜呢。我们出去了,可以轮流养活爹嘛。四个儿子,一家三个月,一年不就过去了?老三无奈,只好对爹说,爹,现在村里要在公路两旁修铺面,办村级市场,我想也批一个,办个修理铺。只是我们一走,这院里就……..没等儿子说完,他就说,这是好事,你们走吧,我还能动弹动呢。老三把自己的两间也拆走了。老院子就只剩下他住的两间,孤伶伶地圪蹴在儿子们拆剩的破墙烂垣之中。儿子们走了,谁忙谁的去了。他除了经营两个牲口,就是清理院子里的破砖烂瓦。把儿子们拆下的垃圾一车子一车子推出去倒掉。还能用的收拾在一起码放好。经过一个多月的劳作,院子里又宽宽展展的了。他还在腾出的屋基上整出一片地来,上了粪,挑水浇了,种上蔬菜。一天的日子就忙忙碌碌的了。
儿子们虽说都搬出去住了,还是隔三天你来隔五天他来。媳妇、孙子们也三天两头过来,拔个菜,要个好吃头。小四三月两月写个信,寄点钱。日子就这样不快不慢地过着。
儿子们很争气,没有几年都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去了。老大成了个小包工头,在花土沟、芒岸等地搞修建,听人说一年挣个十万八万的;老二当了村主任,二媳妇开了一个杂货铺子,生意好得很;老三起先搞修理,后来开始卖摩托,再后来嫌来钱慢,就买了台联合收割机走南闯北去了,老三媳妇把修理铺重新装修,改成饭馆,请了厨师,她自己当起了老板娘。小四也娶了本单位的姑娘,成了双职工,一月两人收入也很可观,买了楼房,生了个女儿。
老汉很惭愧,也很自豪。惭愧的是自己没有给儿女挣下个象样的家业,自豪的是儿子们都比自己强。他觉得自己一辈子的苦没有白受,孩子们都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各奔前程,也对得起死去的老伴了。就是死了,也能体体面面去见她了。
有一年春节,小四回来了。非要请他去玉门住些日子不可。他说,我走了,牲口谁喂?儿子们说,现在庄稼地里都不用牲口了,爹年岁也大了,牲口就处理掉去吧。他只好听儿子们的,把一个驴,一个骡子一个猪和十个羊都处理了,卖了五千多,给四个儿子一人一千,自己留了一千,就跟上小四去了玉门。
没有想到的是,他享不了城里人的福。首先一条是他行不下大便。看到铮光瓦亮的座便器比自家的锅台还阔气,怎么也下不来,又不好给儿子媳妇说,只好每天跑许多路去上公厕;二是一天啥事情没有,吃了睡,睡了吃,电视又看不大懂,下楼去吧,又怕转了向找不回来;三是媳妇每天都要他洗脚,三天两天要他洗澡。一天坐在阴凉房里,风不吹,尘不起,有啥洗头呢。四是媳妇不让他在家里抽烟,烟瘾来了要么到楼下去,要么在厕所里。还没有一个月,就受不了,死活不住,要回老家去。小四没有办法,就把他送上火车。
老大开车把他从车站接回家。老大说,爹,这次来就在我们哥三个的家里转“猪头”吧,一家四个月。老院子你就不要再去住了,你一个人住那,我们也不放心。那里暂时就先放我的车辆和设备吧。他心里还想一个人住,但又怕伤了儿子们的心,就决定在三个儿子家轮住。
于是他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无产就无产吧,儿孙的,也就是自己的。只要有饭吃,冻不死,就行。他想。
他吃上了派饭,一个儿子家四个月。在谁家吃住,就给谁家操心干活。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想他的老房子老院子了。还是觉得一个人过好,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想啥时候出去就啥时候出去,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村里的老哥们,谁来就来,坐一块喧喧谎,掀掀牛九,高兴了还喝上几口。现在住儿子家,就得随人家。这家刚适应了,又到那家,一家一个行事,只得又随人家的习惯。干活倒是不怕,一辈子就是个干活的命,可老啊老了,却失去了自由!他几次想提出一个人去住,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不自由就不自由吧,过一天就少一天,见天的日子少了,见地的日子快了,到哪天阳寿一尽,尿脐子一朝天,一辈子人就算完了,何必再给孩子们找麻烦。想到这,他就又觉得活人嘛,怎么活也就一辈子,将就着过吧,真要到病了,瘫了的那一天,不还得回来吗。
他听说乡敬老院不错。就去了一趟。有十几个老人,两人一间屋子,有人管理,有专人做饭。吃过饭,坐在一起打牌的,聊天的,出去散步的,嘿,满自在的。
回来后就告诉儿子们,他想去敬老院。
我们的这个老爹啊,你真是活糊涂了!老二说,你是没后啊还是我们不孝顺。你去敬老院,不是给儿女脸上抹黑吗?真是的!
是不能给儿女抹黑。他还真没有想到这一层,敬老院不是谁想去就去的。那就只好继续他“转猪头”的日子。
就在他努力适应各家的“新时代”的时候,一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小送了人的老五跑回来了!他说,养父母都病死了,养父临死时告诉了他的身世,写了地址和他生父的名字,让他来找他。
一家人全都傻了眼!大家谁都清楚,老五一个大小伙子,赤手空拳地回来,势必要给大家增加负担,除了眼前的衣食住行,马上面临的是娶媳妇安家。真是安稳不安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老五的突然回来,像一击重拳,把老汉几乎击倒。有啥办法,儿子从小被送了人,现在混不下去,自己找回来,怎么能不认或拒之不要呢?可是从三个儿子、三个媳妇的眼里,老汉看得出来,他们都不愿意接收这个不期而至的同胞弟弟。他给玉门油田上的老四打电话说了,老四说也只能面对现实,家里怎么安排就怎么着吧。
真真切切是自己的儿子,你能推给谁去!也好,老汉决定和老五回自家的老院子。儿子媳妇们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慷慨大方地凑了些应手使的家具和粮米油盐,一家出了一千块钱,给他们父子俩重新安了家。
老五的回来,使他陷入到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窘况中。
老五和他没过上一月,就出现了感情危机。这个孩子从小在人家长大,除了血统,没有一点他们老范家的影子。说话、做事、生活习惯、性格脾气他都看不惯,但他还是迁就着,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说一下。说轻了他不吱声,说重了他不接受。一次居然怒颜相向:“有本事日,没本事养,你有脸说谁呢?”这句话,使他几乎背过气去,同时也把父子的情感危机公开化了,父子之间就成了路人,相互之间无话可说。父亲毕竟是父亲,事后一想,也是话丑理端,孩子从小送人,现在又回来,十七八岁的人了,一无所有,没有怨气才是怪事。气归气,还得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他去找老大,想让老五去他的工地。老大答应了,说是先去干活,然后慢慢考虑给个好一点的事做。
老五一走,他觉得轻松了许多,又来了信心,先是种上了自己的几亩地,又买了一个口轻的草驴,让王大宝的种马配了骡子。一天手不离缰,比侍候老婆坐月子还精心地侍候着。心里盘算着,一年一个骡子,加上庄稼地里收入,也弄个六七千块,再加上老五挣的,每年能有两万来乎的收入。省吃俭用,三年就可以给老五说婆姨了。
可是老五实在不争气。苦活累活不愿意干,有技术的活儿又干不来。老大没有办法,就让他在工地上看材料。可倒好,他来了个监守自盗。晚上常常把钢筋啊,模型板啊,水泥啊啥的,弄出去卖钱,然后不是下馆子,就是上卡厅,再不就是招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打麻将,喝烧酒。不到半年,就被老大辞退回来。回来后,白天睡觉,晚上就出去了。他不敢问,也没心思问。猫老降不住鼠了,有啥办法。他担心老五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果然,一年不到,涉嫌盗墓,被判了两年徒刑。
想不到的是,老五两年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一天沉默寡言,埋头干起活来。尽管和他的关系还很冷漠,但他还是感到欣慰。他知道,感情的事情,是历史造成的,不是老五的错。所以他也不怪儿子。只要儿子能痛改前非,好好做人,他还是愿意拼上自己的老骨头帮助老五。他又去求老大。老大还犹豫着,老大家的却坚决不答应。说,宁给个三千五千,也不让老五再去。最后老大、老二商量了一下,说,你去和老五说,他要是能选个正经事情做,我们四个哥哥愿意帮他。
他和老五说了。老五说,我也不知道干啥好。你说干啥好呢?
他说,娃子,我思谋着,还是养羊行。只要下苦,一两年时间就有起色了。干这,我是行家,你四个哥哥也愿意帮你。
老五想了几天后,就答应养羊。老大就和三个弟弟商量了一下,四个人凑了两万块钱,帮老五养羊。老五不会放羊,就做一些备草,粉草,磨料,修圈,搭棚,起粪、垫圈等的杂活。他就一年四季赶着羊群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两年以后,他的羊就发展到200多只。每年卖掉七八十个,加上羊毛,纯收入不下三万。
就在他开始盘算给老五翻修房子,物色对象的同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不到日落归圈的时候,他就觉得腿不是他的腿,脚也不是他的脚了。一旦坐下,就不想起来。这些羊似乎也感觉出了他的衰老,觉得主人的威慑力在逐渐减弱,他扔过来的土坷垃没有先前那么准那么有力,他对它们的指令也疲疲沓沓,有声音,没力度。所以,慢慢地,羊们也就爱听不听的了。有几次它们居然在他的喝令声中抢到人家的庄稼地里赶不出来。即使他扬起牧棍敲打它们,它们也不怎么惊慌,该吃庄稼还吃庄稼,该不听话还不听话。
他掐指一算,吃了一惊!乖乖,怪不得呢,都七十二了!
他就这样死撑硬扛地坚持到冬天。在他赶着羊群去芦草沟饮水时滑倒在冰滩上,一条腿就骨折了。
常言到,久病床前没孝子。谁都能想象到,他卧床三个月的情景。自己又没有生下个女子,老伴呢在刚生下老五就大出血死了,媳妇们至多给你端个饭,三日五日过来一趟,站得远远地问侯一声;儿子们也是,谁有谁的事,不可能时时守在旁边。老五还得每天去放羊,常常一整天不见一个人影。他就躺在床上审视自己的过去,实在也觉得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缺德事,怎么老了却遭此大难。与其这样,还不如一跤摔死。这样不死不活,受到几时呢?
最终他还是站起来了。
最终老五还是翻修了房子,也成了家。女人倒是个能下苦,有心计,会过日子的人,家里的,地里的独立承担。老五就专心放羊,夏天里进山,冬天里下滩,很少回家。
他成了留守者。拖着一条废腿,扫院子,喂鸡,喂猪,填炕,再就是提个芨芨筐房前屋后拾点粪,村头地上刮些草。到媳妇快收工的时候,把火生旺,水烧开。
再后来,手脚越来越笨,记性越来越差。喂鸡,鸡跑出来,鸡屎拉得满院子;喂猪,猪把食盆拱翻,火也生不旺了,炕也烧不热了。
儿媳妇先是挂个脸,风风火火地干他没有干好的活,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委屈地站在一旁。后来,媳妇就憋不住了,一边干着,一边就比猪骂狗。再后来有了孙子,媳妇娘家妈来侍候月子,他就完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有时候打听得老大老二他们在家时,就去转转,想和儿子们说说话。可儿子说,你都七八十岁的人了,瘸瘸拐拐地,不在家里好好待着,到处乱跑啥呢?不小心再摔了咋办?于是儿子家里也不敢多去了。就又和村里的老人们聚一块说说话。被媳妇瞧见,就都捎带上说,吆,人老没出息,不是说儿子,就是骂媳妇。谁家的又不孝顺了?于是谁也再不敢和他来往。
有一次,邻居家小孩来借打气筒,他就借了。人家用罢忘了还。媳妇要给自行车打气,怎么也找不着,问他,他也忘记了。后来媳妇在那家看见了,就要回来,啪地一声,摔在他的面前说,这东西长了腿了,咋到赵瑞家了?不知道还有啥东西叫人来拿走了呢!养个狗,来个生人还知道咬几声呢,一个大活人放在家里,连个门都看不住了!
从此,媳妇出门时,就把所有的房门都锁了。把鸡啊,猪啊的食料放在窗台上,让他按时喂上。他就像一条老狗,守在空落落的院子里。
国家给农村老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他听说自己也有一份,但从来都是儿媳妇去领。
那年三月,媳妇领了他的低保金,把孩子送到娘家,就给自己的男人办了些伙食,赶着骡子车去了山里。两口子长时间没在一起了,那天晚上她就住下了。第二天走出窝棚,才知道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出山的路被雪封得严严实实。男人把羊赶出圈,让羊拌着深雪去啃那些露在雪上的柴棵稍子。两口子就宰了一个十几斤重的羊羔煮上,然后就在热窝棚里继续一夜还没有过足的夫妻生活。
第三天起来,女人挂念着家里的猪啊鸡啊的,要回去。男人就在前面领路,女人使着骡车在后面跟着,出了山。女人走了,男人返回羊上。
女人推开街门,院子里的雪丝毫没动。心里就来了气,一个大活人,留在家里,雪都下了几天,连个人走的路都没有扫开。她卸了车子,栓了骡子,添了草。去开门时,才发现门上还吊着锁子!她就赶紧去了后院。
女人被后院的情景惊呆了!
后院的猪棚被雪压塌了。猪和他都被压在下面,猪死了,人也死了。他的手里还提着给猪添食的桶子。
女人吓坏了,刚要出声叫人,又赶紧忍住了。她急急忙忙跑出来,站在自己的庄门口前前后后地看了一下,然后锁了庄门,向山里跑去。
两口子连夜把羊群赶回来。先把他抬到他睡的屋里焐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上寿衣,用白布带子把他伸着的胳膊和身子捆在一起,盖上红被面子,停放好。再摸黑把后院子打扫了,把一切都收拾妥当,才向哥哥们报丧。
儿子们听说爹死了,都来点了纸,磕了头。谁也没有揭开看他,也没有问及病了多久,怎么死的,平常得就像是别人家死了老人。接着就开始商议如何发丧的事情。
老大说,我们弟兄们现在在地方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老二又是村主任,老四还是工作的。老爹活了一辈子简单人,他的丧事说什么也不能简单。
就听大哥的,老二说,要办就要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通过爹的丧事,显示一下我们老范家在村里的实力。
大哥二哥说得对。你们策划,我们就照着办。老三说,老四明天就到,他肯定也没啥说的。
意见高度统一。
当天就请了本乡最有名气的刘家道士。批了丧条,上面写上亡逝者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及开悼、下葬的地点、日期和孝子们的姓名,贴在板子上,立在街门外面,正式向外界宣布他的死亡。接下来就去苏木匠那里定了棺材。要求是金匣套,板厚三寸,五天交货。再就是统计要请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乡党,好预定酒席。
老大说,亲兄弟,明算账。客一块待,礼分开收。最后根据花费和各家来客的情况分账。我先把话说到前头。老亲的礼集体开支,缺额多少,五家平均分摊。你们各家回去预计你们要请的客,赶明早报个数字,好定桌数。我看就把我们村的张师傅定下。人家是流动餐厅,你把标准和桌数给人家,到时候吃席就行了。席的标准不能低,我看定380元一桌的,加上烟酒就400过了。同样的菜,城里就四百八九五百呢。临时厨房就搭在老五的后院里。前院也要搭住,设立灵堂。老五你去山里砍些松枝,扎个彩门。今天晚上我去东坝里请老阴阳张文博,明天一早我开车去花草滩选看新茔地。
老三说,大哥,我们的老坟不在红山吗,咋在花草滩看新茔呢?
老坟已经不能再进人了,再说旁边修渠,把脉气挖断了,对后人不利。我们族里不出文化人,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的社会,光有钱算个啥,社会上没地位,还是低人一等。花草滩远是远些,那里葬的人不多,有好地方。人说出在门里,葬在坟里。茔地不好,能出啥人?那个地方几年前我就找人去转了一圈,大致选了几处,明天请张阴阳下下罗盘,定定位,选一块风水好地,重新开茔立祖。现在有车,多走几十公里算个啥。
好,就依大哥。弟兄们一致赞同。
他的丧事在儿子们的料理下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切道场都按当地的最高标准。开三、引午,撒灯,放食,诵经,祭拜,焚纸,跪迎,摆祭,领牲,一样不拉的进行。纸楼当门高挑,白联黑帐,挂满庭院,花圈层层叠叠,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哀乐声声,哭声阵阵,不过这哭声从录音机里发出来的。整个丧事纷繁复杂。
在第六天开悼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谁也想不到,谁也不曾经见过的奇怪事。
这一天所有的亲朋乡邻都来悼唁。上午十点,在一片唢呐声中,殡仪开始。在大宾先生的喝吔声中,所有孝子孝孙披麻戴孝,长子在前,其他孝眷依次跟随,手柱丧棒躬身绕灵柩三叩九拜。拜毕,各路亲戚开始摆祭。尤其五个媳妇的娘家为给自家女子争脸,所摆祭物,柔毛盒供,祭纸祭合,清酒香帛一应俱全,琳琅满目,海海满满。令来宾赞不绝口,更让那些老者们羡慕不已。老范一辈子啊,有今天的排场,值了!
然后是领牲。五个儿子每人一只羊,要在父亲的灵前献牲。先从老大的开始。人们拉过一只大羯羊,站在灵桌前,主持者拿水在羊身上一浇,就说,领吧,领吧,这是老大的孝心。你一辈子虽然说没有容易,可五子成龙成虎,哪个不是人前头的人?领吧,领吧。起牲的人在旁边候着,只要羊一抖毛,就立刻拉到外面宰杀,剥了皮后,囫囵献在灵桌前。
那只羊东张西望,惊恐万状,就是不抖毛。主持人说,孝子们,磕头,磕头!拿表来燎一燎。孝子们一起磕头。齐声说,爹,领吧!领吧!弄了半天,又是倒水,又是浇酒,羊已经成了落汤鸡,但就是不抖毛,不领。没有办法,主持人只好说,咋不领呢,对了,可能是心疼老大花得多了。那就这只先拉过去,让老二献吧。老二的大羯羊比老大的还要肥大。你看,儿子们给你献的羯羊一个比一个肥壮,儿女的孝心全在这里了。领吧!领得喜喜儿的。老二的羯羊也被浇成了落汤鸡,还是丝毫不抖一下毛。老二就说了,爹啊,你还有啥不满意的呢,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村谁的丧事有你的排场呢,你就不要为难我们了,领吧。你看,亲戚们还等着坐席呢。主持人说,不领的就先拉过去,后面的来,谁的领了就先起(杀)谁的。老三,老四的也都不领(抖毛)。人们傻了眼。大家私下议论开了。真是蹊跷,没有见过,哪有一个都不领的呢?老汉可能有啥不满意的地方?最后看看老五家的领不领?
人们把希望全寄托在老五家的羊上。这是一只白身子黑头的大羯羊。村上的人都知道,这是范老汉精心务习下的。这只羊丝毫没有恐惧的样子,气宇轩昂地站在灵前。当主持人把水倒在它的身上时,它一个激灵,跳起来,一头撞翻了灵案,桌上的祭品满地乱滚,点着的蜡烛把桌下的祭纸燃着,乎地一下大火烧起来。羊趁人慌乱中跳出人圈跑了。人们惊慌失措,救火的救火,捉羊的捉羊。就在丧事乱成一团糟的时候,老五家的突然疯了,又哭又骂,拿起老汉生前扫院子的扫帚,乱打乱扫起来。吓得妇女孩子哭喊连天,东跑西奔!
老五急了,冒着被打的危险,扑上去把自家媳妇拦腰抱住,按到在地,才控制了事态。
人虽弄住了,但嘴却仍在乱说乱骂,而且好像是范老汉的口气。人都死了,你们献羊干啥,啊?献上谁能吃上你的一口啊?活的时候谁给过一口肉,啊?现在我死了,你们倒孝顺成这个样子!老子都死了两天了,你们连个鬼面都不见啊……
人们从这些含糊不清的叫骂中,隐隐约约知道了老人的不幸和死因。
就在老范的儿子们手忙脚乱地收拾尴尬局面的时候,来参加悼奠的亲朋好友,邻居乡党,全都不辞而别。五兄弟摆的六十桌席几乎没有人坐。
第二天早晨,村里一家一个人来,把老人送到花草滩的新茔地里。
五兄弟的五个羊也没有再献,六十桌席,一家十几桌分了。这几家人每天吃席,一直吃到连猪和狗都倒了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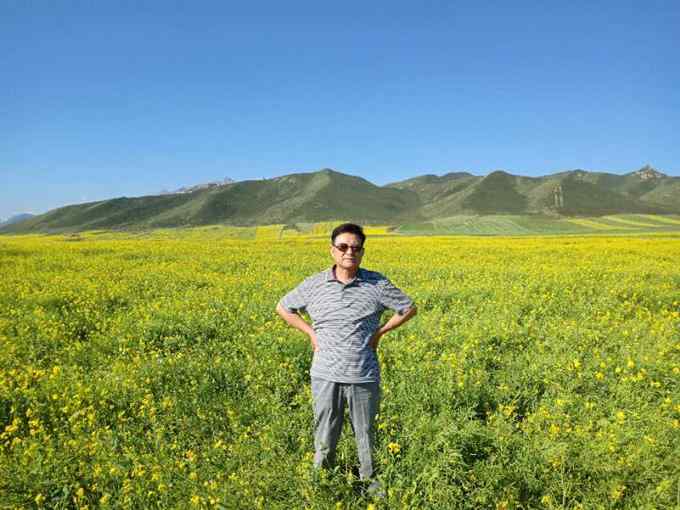
作者简介:郭勇,甘肃山丹人。山丹县文联退休干部。先后在《飞天》、《星星》、《散文选刊》(下半月)、《北方作家》、《六盘山》《雨花》《少年文史报》《中国环境报》《甘肃人大报》《政治协商报》《中国少年科技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论、杂文等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获奖。出版散文小说集《昨天》(中国文联出版社)、《山丹民歌谚语选》(中国文联出版社);《山丹宝卷》上下卷(甘肃文化出版社。与人合作出版)。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选刊•下半月》签约作家。
责任编辑:周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