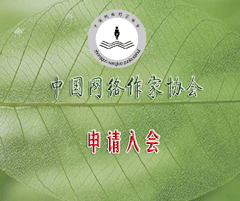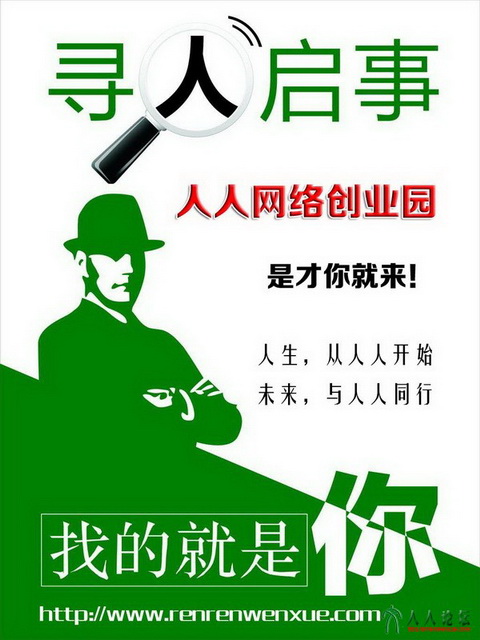|
静妃——后宫的那一抹暖阳 整个的后宫里,静妃像是一抹冬日的暖阳,一直温柔明净的存在着。 她不是世族,没有娘家作外援,她这样的出身,其时不好进宫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包括生活习惯,都不适合。只是为了恩义吧,为了林帅当年的救命之恩。因为宸妃生了祈王身体不好,她被以医女的身份送入宫。最初有了林家的照看,日子应该不难过。后来有了儿子,希望算是有了。只是自小游历山河的静妃,决不会爱着那个宫规森严风刀霜剑的后宫。 她是后宫中最冷静的女子,一直以一种游离的姿态存在着,她爱着她的医学,所以所居的芷萝宫药香阵阵,这是她的寄托吧。她以这一种方式保留了心底的坚持。 如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构陷,她的人生就在宫里平静如水渡过,不争宠不介怀,在宸妃的关照下,在儿子的支撑下,这也算是平顺了。 那时的惨烈,祈王死了,宸妃死了,晋阳长公主死了,赤焰军没了,林家父子没了。这样的变故,几乎是静妃的世界完了。唯一的庆幸是景琰还在,她的希望还在。 此后,她低眉转身,退居芷萝宫,低调,隐身,让皇后和越妃在前台明争暗斗,她只求活下去。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这一隐就是十几年,最美好的年华,都隐了。 在出场时,是为了体贴被皇后责难的惠妃,一起去佛堂,听闻了情丝绕,她马上明白了,她们的目标是被皇上弄进京招亲的霓凰。那是故人之子林殊的未婚妻。 情深意重的一直坚守着当年的婚约。她自然要管,只是以她的身份和能力,根本不好约见郡主。只好以香囊示意长公主。兰心慧质一出手,就是沉稳精明。 说动长公主也是一番情真意切。为什么选长公主,因为长公主当年深受其伤,因为长公主是林殊的故人。因为长公主能担待肯担待。看事要透,看人要准,所托才不会成了空。为了小殊,她输不起。 静妃的平静日子是被儿子打破了,景琰为了小殊,要踏入夺嫡之路。这条路的艰难,静妃比儿子明白,当年的祈王被皇上犹疑,自然也有如今的太子加入其中,也是夺嫡的余波罢了。而且景琰现在是弱势 ,太子名正严顺,又有越妃相助。而誉王机敏玲珑又得皇后扶持。最弱的反而是这位郡王了。自身个性刚直,母亲目前又只是一个嫔位。朝中也无人支持。个中强弱,对比分明。可是景琰的志向,就是一个母亲的志向,她果断的支持。并坦然相告,自已有自保的能力。 静妃那般爽利的支持景琰,也有着替林家洗冤的意思吧。按如今的形势,不管是太子,还是誉王上位,都不会还林家清白。只有景琰能够。 她的镇定从容,给了景琰力量。让他有勇气往前走。 既然拉开了大幕,她也要相助景琰,于是芷萝宫的药香引来了皇上。她进了宫斗的战场。 与皇上很多年没有如此闲话家常的时光了,却深谙如何奉承这位满腹心机的人。不是她不能得宠,这么多年是她不肯。 随后而来的荣耀,其实为了提升景琰的身份。晋静嫔为静妃。 只为了一本《翔地记》就能判断出苏先生就是林殊,这是心细发处。最聪慧的是,她能无声的配合长苏瞒了景琰。既然小殊不说,自然有不说的理由,她相信对方的苦心,是为了景琰好。于是一直不说。就是儿子几次三番的追问,也能沉默似金,不破坏长苏的大计。这是一个沉得气的人。大事上,清醒冷静。 作为一个长辈的关怀却是细致如微了。十几前小殊的饮食习惯,依然记得。此后送去的点心,都是不碰小苏的忌讳。以这种方式婉转的暗示,她知道他是谁。所以长苏相信静妃就是知道了,景琰也不会知道。 只是一次次提醒,景琰善待长苏,肯定长苏的心性为人,必然是霁月清风一样的好男儿。婉转的劝说,只是怕景琰日后会遗憾。 她冷静自持,只是猎宫故人会,才真情流露,再不能从容。 静妃摇头道:“这几日不比家居。你时常要帐内帐外地走动,如果里面极暖。外面极冷,只怕更易成病,帐内还是多通气,确保温度适宜的好。”(怎一个体贴是好,长辈对晚辈一向是如此,怎么关心都不够) “娘娘果然深谙保养医道,”梅长苏欠了欠身,“我家里也有一位大夫,只是这几日没有随行,我只好一味地保暖,多谢娘娘指点.(长苏还在维持着镇定和礼仪) “先生冒风而来,不宜饮此茶。”静妃随即扬声召来侍女,吩咐道,“去取紫姜茶来。”(关心入微,只是此茶令有深意) 侍女领命而去,不多时便捧来一个紫砂茶壶和一只小杯。梅长苏见静妃起身亲自斟茶,忙谦谢道:“怎敢劳动娘娘,请这位姐姐斟吧。” 静妃浅浅一笑,命侍女退下,端起茶杯道:“先生为景琰如此尽力,我礼敬一杯清茶也是应该地。”说着便将手中小杯递了过去,谁知一失手,杯身滑落,姜茶水飞溅而出,全都洒在梅长苏的袖上。(她是奇怪,长苏因何容颜大变,想要看胎记) “哎呀,先生烫到没有?”静妃忙摸出手巾为他擦拭,靖王也赶了过来。 梅长苏知道静妃之意,心中有些酸楚,于是没有闪躲,由着她趁势将自己的衣袖卷起。(聪明人就是好办事,能互相配合。) 静妃看到那光滑无痕的手臂时,表情与霓凰郡主一模一样,只是她的情绪更加内敛些,怔怔地后退一步,便没有了更多地动作。“苏某并未受伤,娘娘不必在意。”梅长苏将视线移开,低声说了一句。靖王扶着母亲回到原位,神色有些疑惑,想要问,又不知该问什么,犹豫了一下方道:“母亲今天好似神思困倦,不如休息一下,我与苏先生改日再来可好?”(他的母亲一向冷静,今时连连失态,令他奇怪。) 静妃若有所思,竟没有理会儿子的话,沉默了片刻,突然又对梅长苏道:“苏先生那本《翔地记》,我很喜欢。上面提到涂州一处飞瀑,我看先生的批注,应该是去过那个地方的吧?” “是。” “听书中描述,此瀑飞流直下,气势壮观,恨我不能亲见。不过我一时记不太清,这飞瀑到底是在涂州的哪个县府啊?” 梅长苏的视线微微一颤,抿紧了嘴角。涂州溱潆府,十分简单的答案,却是亡母的闺名。他虽然知道静妃此问何意,却又终究不能坦然出口,所以迟疑了片刻后,还是无奈地摇头,“苏某也不太记得了。” 静妃静静地凝望着他,不知因为什么,眸色变得澄澈而又忧伤。靖王有些不安地看看母妃,问道:“母亲很想去看这个瀑布吗?孩儿倒还记得,那个地方是……” “你不必说,”静妃快速地截断了他,“我问问罢了,哪里出得去?” “娘娘现在身份贵重,确实不能随意出行,只能委屈些,留作遗憾了。”梅长苏垂下眼帘,劝了一句。 “身份贵重……”静妃郁郁一笑,容色有些黯淡,“不说这个了。我看先生气促不均,面色透白,病势应已缠绵了许久。平常都吃什么药?”“是些调补的药吧,我也不太懂,都听大夫地。” “我倒还略通医道。先生不介意的话,可否让我切一切脉?(她要知道小殊的身体状况)” 她当着靖王的面这样说。梅长苏当然不能介意,反而是萧景琰从旁劝道:“母亲,苏先生身边已有名医,您不必……” “我只是切切脉,又不扎针行药。有什么打紧地?”静妃柔柔地一笑,“你不知道但凡医者,都想多见识几个病例吗?” 靖王知道母亲性情虽温婉,可一旦开始坚持什么,就很难改变,只得起身,将她的座椅移至梅长苏身边,又取来一只小小地枕包。 梅长苏地双手,在袖中微微捏紧。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当然清楚,可是他却不知道静妃地医道已修到了什么程度,自然也就拿不准这只手一伸出去。秘密是否还保得住。 不过此刻的局面,已由不得他选择。静妃幽深哀凉的目光。也让他无法拒绝,所以最后。他还是缓缓地将左手手腕平放在了枕包之上。(在静妃面前,聪明如长苏也主导不了气场。) 静妃宁神调息,慢慢将两根手指按在了梅长苏的腕间,垂目诊了半日,一直久到让人觉得异样的地步,手指方缓缓放松。 靖王躬下身子,正要开口询问情形如何,谁知定晴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只见静妃将手收回后,回腕便掩住了朱唇,翻卷地长睫下,泪水如同走珠一般跌落下来,止也不止住。萧景琰已有多年未曾见自己这位淡泊宁静的母亲落泪(前情如此,怕是当年梅岭之事后),心头自然大骇,立即屈膝跪下,急急问道:“母亲怎么了?如有什么不舒心的事,尽可以吩咐儿子去料理……” 静妃深吸着气,却仍是止不住地抽咽。越是平日里安稳持重的人,一旦情绪决堤,越是难以平息。她扶着儿子的肩,凭他怎么问,也只是落泪摇头,哭了好一阵,才轻声道:“景……景琰,你今日……可有去向父皇请安?” 她哭成这样,却问出如此一句话来,靖王一时更加无措,“我与父皇……上午一直在一起啊……” “那下午呢?” “还没有去过。” “你……去向父皇请安吧……” 靖王呆了呆,道:“父皇不是在午睡吗?” “午睡也该去,”静妃断断续续地道,“至少等、等他醒了,如果听内侍说……你来过,心里一定……会高兴的……” 萧景琰怔怔地看了母亲半天,突然明白了她的用意,迅即转头看向梅长苏,却见这位谋士已站了起来,静静地避让在一边,整张脸如同戴了面具一般,瞧不出丝毫端倪。 “快去吧,去吧……”静妃拍着儿子的胸口,缓慢但坚决地将他推了出去(此时此景,还记得长苏的身份不能令景琰知晓),但等他走后,她却又没有立即跟梅长苏说话,反而是跌坐回椅上,仍是珠泪不干。梅长苏无奈地凝视了她片刻,最终还是悄然长叹一声,缓步上前,蹲在她膝前,摸出袖中软巾为她拭泪,轻声道:“娘娘,您别再哭了,再哭,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时候,长苏是不能再装了) “我知道……只是忍了这些年,突然忍不住了……”静妃似乎也在拼力地平息自己,拉着梅长苏让他坐在身边,泪眼迷蒙地看着他,看一阵,又低头拿手巾擦擦双眼。“我现在很好,”梅长苏柔声安慰道,“只是比常人稍稍多病些,也不觉得什么。” 静妃哽咽道:“火寒之毒,为天下奇毒之首,要清理它,又何止脱一层皮那么简单?为你拔毒的那位医者,可有说什么吗?” “他说……我底子好,没事地。” “怎么可能没事?挫骨削皮拔的毒,第一要紧的就是静养,”静妃一把抓住梅长苏地手,恳切地道,“你别管景琰了,好好养着,京里的事,我来办,你相信我,我一定办得成……”(终是心疼小殊,连景琰的夺嫡都不让长苏参与了,她是真的在意这个孩子。那一句我一定办得成,也是有底气才说。她知道儿子和小殊在忙什么,她懂他们的心意与志向,那也是她的心意。) 梅长苏用温暖而又坚定地目光回视着她,缓缓摇头,“不行地,宫里和宫外,毕竟不一样……我走到这一步,已经越过了多少阻碍,娘娘,您也要来阻碍我吗?” 静妃心头如同被扎了一刀般,更是止不住的泪如泉涌,仿佛压抑了十几年地悲苦之情,全选在此刻迸发了出来。 “您若要帮我,就什么也别跟景琰说。”梅长苏的眼圈儿也渐渐地红了,但唇角却依然噙着淡淡的笑,“景琰很好,我也没有您想的那么累。您放心,我有分寸的……您以后还是继续给景琰做榛子酥吧,就算他不小心拿错了,我也不会糊里糊涂随便吃的。” “小殊……小殊……”静妃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轻轻抚摸梅长苏的脸,“你以前,长得那么象你父亲……”(故人不在眼前,唯一的儿子,成了这副模样,岂不伤情。) “娘娘,我们不说这个了。”梅长苏继续给她拭泪,“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您会帮我的,是不是?” 静妃透过一片模糊的水色凝视了他许久,最后终于一闭双眼,缓慢而沉重地点了点头。 见她允诺,梅长苏的唇边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明明是宽慰的表情,却又显得那么悲凉。静妃不忍再看,低下头,用手巾捂住了脸。 “娘娘,”梅长苏缓缓站起身,轻声道,“时辰不早,我也该走了。您一个人能静下来吗?” 静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力印干脸上的水迹,抬起了头,“你放心。景琰那边,我知道该怎么办。” 真情流露的静妃娘娘,代表着长苏那些温情良善的长辈们,她们给过他温暖和幸福。而今,只有一个静妃了。 静妃果然说到做到,一直在心生怀疑的景琰面前隐藏了小殊的身份。 最后金殿要求重审那一节之后,皇上恼恨景琰母子,此时静妃依然在劝说皇上,够胆识够沉稳。而且字字珠玑让人震憾。 “把陛下唤醒吧,又在做恶梦了。”静妃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殿中,温和地发出了指令。(依然是贵妃风华,她太清楚皇上的心结了。) 高湛赶紧应了一声,爬起来,俯身到床前,轻轻摇动着梁帝的手臂。 “陛下……陛下!!”连喊了十几声后,梁帝突然象是被什么东西震了一下似的,猛地弹坐了起来,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满头大汗淋漓。陛下又梦见什么了?”静妃用一方素帕轻轻给老皇拭着汗,柔声道,“这次应该不止是宸妃,还有其他人吧?”(一定会有林帅,一定会有长公主,那些曾经的故人,都是他曾经生命中相随一时的人,很重要的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梁帝全身一颤,用力挥开了她的手,怒道:“你还敢来见朕?枉朕待你们母子如此恩宠,你们竟然心怀叵测,处心积虑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宠信了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此时还在硬撑。)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静妃安然道,“可是有一点陛下必须清楚,赤焰一案之所以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积心积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平静的解释。) “什、什么原因?” “真相。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静妃的目光如同有形一般,直直地刺入梁帝的内心,“陛下是天子之尊,只要您不想承认今天所披露出来的这些事实,当然谁也强迫不了您。可即使是天子,总也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在梦中向您走来的那些旧人……”(掷地有声的评述,这是静妃的认知,真相是永远挡不住的,谁也不能,公道自在人心。这是静妃的底气与公义吧。) “别再说了!”梁帝面色蜡黄,浑身乱战,两手捧住额头,大叫一声向后便倒,在枕上抽搐似地喘息。(这是皇上的心结。) 静妃伸出一只幽凉的手,轻轻在梁帝眉前揉动着,低声道:“陛下,若论忠孝,林帅不可谓不忠,祁王也不可谓不孝,景琰素来以他们为楷模,他们当年没有做的事情,景琰也绝不会做,请陛下无须担忧(安心,皇上就是介意他的皇位,只要不动他的宝座,一切还能谈,现在是承诺)。” 梁帝慢慢松开盖在脸上的手,定定地看向静妃:“你敢保证吗?” “陛下若真的了解景琰,就不会向臣妾要求保证了。”静妃的唇角,一直保持着一抹清淡的笑意,只是羽睫低垂,让人看不清她的眼睛,“景琰所求的,无外乎真相与公道,陛下若能给他,又何必疑心到其他地方?”(算是一个保证了吧,保证真相与公道。) 梁帝呆呆地权衡了半日,目光又在静妃温婉的脸上凝注了良久,最后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喃喃道:“……事已至此……就由你们吧……朕不说什么了……” 能让皇上妥协,从心里接受,重审赤焰一案,也需要娘娘最后这番开解。最后提真相的时候,静妃的冷静与底气,完全是因为那是她认定的公理,是她一直坚信的公理,那是她的底气。因了这个认知,她才能坚守十几年,才能在景琰夺嫡的时候,坚定的支持儿子。 静妃是后宫的另类 ,始终有自己的良心与生活态度。能坚定的把真相公理放在心底,一直照耀着她的日子。成了深宫的一抹暖阳。 是呀,有的演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质越来越好,有了一种玉的光茫。醇厚温润。比如长公主,比如演静妃的刘敏涛。都是这类演员。言候的演员,演得很深透自如,有气势。看胡歌的演技也是如此,现在看着越发动静相宜收放自如。于他们来说,阅历反而加了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