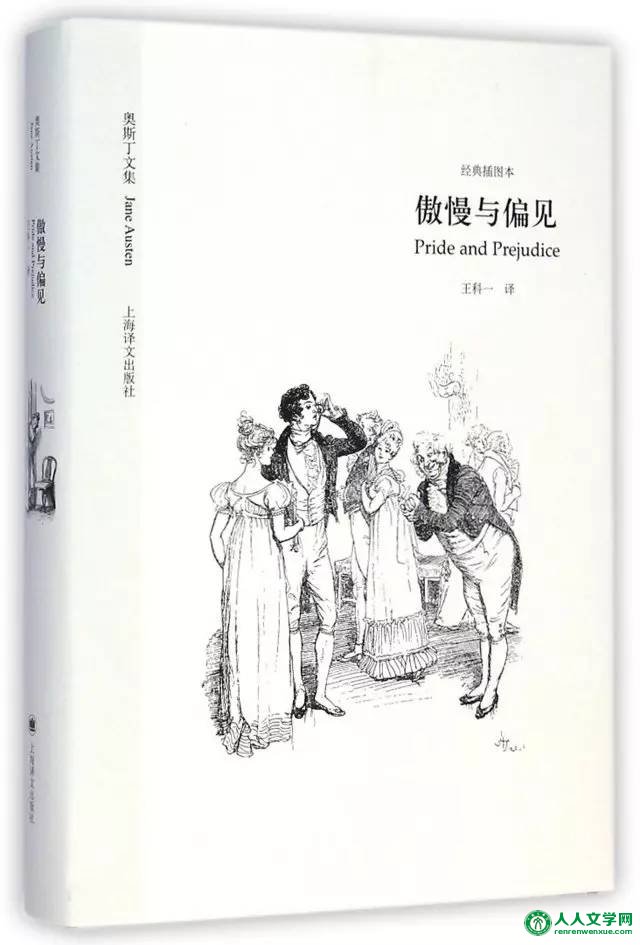|
今天是简·奥斯汀逝世200周年的纪念日。 两个世纪以来,简·奥斯汀一直拥有众多读者,在必读经典书单内长期占据一席之地。而且自1940年开始,她的小说就不断被翻拍成影视剧,不少版本都已经成为经典。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小说家,作品有《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等。她的小说展现了18世纪末英国地主乡绅的生活。图为简·奥斯汀的姐姐卡珊德拉于在约1810年为她绘成的肖像。 但在在文学史上,简·奥斯汀的地位似乎又有点尴尬。她的小说闻名世界,然而好像没有几个人会把这个受众广泛的女作家视为“文豪”,还有不少关于她的批评,认为她的风格太软,题材太匮乏,数量只有6本,格局又那么小,永远停留在乡绅生活的图景里。从普通读者到小说大家,要么称赞她为“女莎士比亚”,要么抨击她的作品一文不值。 转眼间,20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声音,简·奥斯汀已经不可能听到,何况,她生前从来不曾在作品上署过这个名字,她也没有见到自己成为经典作家,她只是个起居室内的舞者,以精彩的动作寻觅理想的自由与上帝。“女文豪”,或许她做不了,同样,她也不屑做。 撰文 | 宫子 “她必须得跳舞……他老坐在屋中,所以要将他排除在外,就要在自己的上帝面前跳舞。在一个礼拜六下午,她又脱掉衣服跳起舞来,舒缓而有节奏地抬膝舒臂,快乐地手舞足蹈着……她在为她本人无形的上帝而起舞。” 这是劳伦斯小说《虹》中安娜在起居室内脱衣跳舞的经典片段,奇妙的是,这个不相干的段落竟如此契合简·奥斯汀的小说世界——一个在日常事务背面写作的小女人,也是一个在自己的起居室内寻找上帝与自由的女文豪——但争议在于,她真的算是女“文豪”吗。
简·奥斯汀故居,位于查顿(Chawton)乡间,是她生命中最后八年的居所。 称“简·奥斯汀”为女文豪或许永远都是件争议的事。她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世界中写作,脱去应对日常俗务的服饰,用寻找内心上帝的姿态翩翩起舞,似乎只有在这个舞蹈的时刻,她才是自由的。 与文学史上其他卸掉日常服饰的人不同,有些人脱去日常的衣物,为的是展示自己强健的灵魂胴体;有些人脱去日常衣物,却披上另一件不合码的概念式外套。简·奥斯汀在文字之舞中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一件透明的舞裙,它仿佛一件反义的“皇帝的新装”,你想要开口称赞她,却无法忽视“高级观众”们的不屑声—— “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只有可嫁性。” “我恨不得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用小胫骨敲她的脑袋。” “她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马克·吐温,夏洛蒂·勃朗特等人都表示奥斯汀的舞裙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你想要跟着这些高级观众的声音否认简·奥斯汀,又实在无法抗拒小说的魅力,无法忽视那件看不见的、却又华丽并令人心动的舞裙。 这二者矛盾吗。并不矛盾。 这就是简·奥斯汀的世界,一个起居室内的小天堂,一个用看不见的心丝制造水晶舞裙的小说大师。
1995年版电影《傲慢与偏见》剧照。 奥斯汀的小说究竟有没有思想? 写作是双向的,对作者,对作品而言,都是一种远行。作者并非单纯的艺匠,而是探索者,一边写作,一边寻找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成形的,或者不成形的。这在简·奥斯汀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每个艺术家想要找到的东西都不相同,有宏大,也有微妙,简·奥斯汀想要在写作中找到的是一种材料,能让她编造出让每个人心灵飘飘起舞的水晶舞裙的材料。不过在写作的早期,奥斯汀并没有找到这种“不可见的丝”,在《理智与情感》中,她使用的是大众化的,可见的丝料,因此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并没有“飘然起舞”的感觉,而是显得世俗且笨重。
《理智与情感》 作者: [英] 简·奥斯丁 译者: 孙致礼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理智与情感》在1811年首次发表,是简·奥斯汀第一本长篇小说。小说的初稿在她19岁时完成,当时命名为《爱莲娜和玛丽安》。 说教,理念,从来都不是简·奥斯汀的特长,也不是她小说的魅力所在,就好像我们不能把个性飘逸的时装套在每个路人的身上一样。她的小说从来不以明晰的思想性或深重的社会反思见长,《理智与情感》属于奥斯汀对思想表述的一次尝试,但并不成功,主人公埃莉诺和爱德华,都好像皮影戏里的人偶,被概念的丝线牵着所以举动十分僵硬。埃莉诺长期用理智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不曾主动追求爱情,爱德华的行为也极为被动,最后两个人的婚姻结合要依靠另一位女性露西的放弃而完成,露西放弃了爱德华,埃莉诺才和爱德华终成眷属。如此被动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在整个奥斯汀小说系列中都是后无来者。 因此,只有当奥斯汀从思想说教的机杼中脱身后,她的小说才最有魅力。这也成了奥斯汀小说受人诟病的原因。缺乏深度,没有广度,没有深邃的思想,皆大欢喜的俗套结局,每一条拎出来都足以冲击“文豪”地位,使人质疑奥斯汀小说的苍白无力,纵使她的小说摆在世界名著行列中,似乎也只是个早生了几百年的琼瑶而已。她的小说地位看起来取决于时间定位而非纵深。
1995年电影《理智与情感》剧照。 所以有很多人不喜欢简·奥斯汀的小说,思想性太差,没有时代反思,故事全都围绕着婚姻铺写,人们希望能从世界经典名著的书架上取出一本真正看起来像莎士比亚的书,有华丽精美的语言,有灵魂深处的拷问,有大悲大喜的命运起落,这个阅读判断的标准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以它来评价“女莎士比亚”的小说就非常遗憾。简·奥斯汀小说从来都不直接构建这些重大命题,自《理智与情感》之后,她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依靠活生生的人物而搭建出来的,相应地,那些让人深思的品性也是完全依靠人物撑起来的。 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作者在小说中不断称赞她“聪慧,独立,有坚毅的性格”,但伊丽莎白身上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象征性的命运转折来映衬这一性格。她就是在奥斯汀塑造的小世界里生活的普通人,没有奥德修斯那种传奇冒险,也没有经历朱丽叶的凄美,她做过最独立的事情可能就是踩着泥泞雨路去探望自己生病的姐姐,她最坚毅的时刻也只是顶撞身份高于自己数倍的凯瑟琳夫人,论及聪慧,她很长时间内被韦翰蒙骗着;其余的时候,她也和其他人一样,呆在家里做些纺织工作,写写信,弹弹琴。
2008年电影《傲慢与偏见》剧照。 可所有喜爱《傲慢与偏见》的读者都不会否认,伊丽莎白是一个“聪慧,独立,有坚毅性格”的女性,她是个让所有人都感到可爱的女性,这是依靠小说中活灵活现的一举一动而渲染出来的。而且,即使没有悲剧,崇高,激烈的命运转折来来映衬,读者依然能从这本日常生活的小说中感受到独立、积极的爱情观。她不像简·爱一样直抒观念,没有安排悲悯崇高的情节,而通过写人物言行,写婚姻喜剧取得了和其他经典作品殊途同归的效果。 这种精彩,已经不是“女文豪”所能概括。“文豪”对奥斯汀来说太沉重,她属于艺术家,她不会去直接写思想,但她的小说一直都在表现思想。在最早的时候,她专写“理智与情感”,效果平平;在最后一部小说里,奥斯汀反其道而行,不再写“劝导”,反而表现出了更有质感的思想——她已然创造了自己的风格。
《傲慢与偏见》 作者: [英] 简·奥斯丁 译者: 王科一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2月 让奥斯汀写大格局,会更精彩吗? 简·奥斯汀的小说人物和另一位公认的大文豪狄更斯有“异曲同工”之处,狄更斯的大世界里只有两种人,好人,坏人,泾渭分明;奥斯汀的小格局中也只有两种人,可爱的,惹人嫌的,没有大奸大恶,大是大非,一切随个人情感而定。 她的小说格局玲珑,不谈社会道德,不讲人间贫苦,却比直接描写贫苦现实的小说更能受到贫苦人的青睐,这便是幻想的魅力,格局虽然小,但并不封闭。在英国曾经举办过简·奥斯汀的读书会,结果去的人里只有一位男性,剩下的都是蜗居在灰色生活里的中年妇女。正是这些生存在现实阴影里的贫苦者,在简·奥斯汀的小说里享受到了幻想带来的最大快感。 是否简·奥斯汀的小说只能吸引这些同样栖居在小家庭里的人,只对那些对家长里短感兴趣的人有价值?按照经典著作的思考方式,一本小说里不是应该呈现更多社会风云,历史洪流,应该写那些与悲剧命运纠缠不休的人文思考?
《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一向被认为满足了女性对男人的幻想。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设想,把奥斯汀的小说格局扩大,写家族变迁史,写时代特征,写冒险与个人英雄主义,结果只可能是更加乏味。因为这些都是现实性的,可见的,而简·奥斯汀小说的魅力在于非现实的现实性——她的小说世界有架空的性质,仿佛从地上悬起来一样。 奥斯汀小说里的家庭日常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日常,这些人家住在彭伯里,诺桑觉寺,或者曼斯菲尔德庄园这样的小领域内,总是忙活着聚餐、旅行、搞舞会、写信、订婚,这么五件事几乎囊括了奥斯汀小说人物的所有行动。这些小格局里的人自由自在地行动,好像永远都不用工作,收入来源要么是领圣职,要么继承遗产。男人们每天坐着马车来回转悠,女人们呆在家里等着爱人上门,总之是全身心投入情感生活。 无论是《曼斯菲尔德庄园》还是《诺桑觉寺》,这些远离尘嚣的地方都是奥斯汀所构建的小乌托邦世界,通过遥望这个她自己创造出的小世界,并赋予人物生命力——宛如女娲造人一样,她也同样脱离了灰暗的现实生活,有了脱去日常外衣、自由舞蹈的小起居室。
2008年电影《傲慢与偏见》剧照。 但这个幻想又绝非哥特式小说那样绝对的非现实。它悬空,但这个悬空的空间内却有足够饱满的现实性。因为悬空,没有多余的连理枝节,那些虚拟人物的言行举止便和舞台背景割断了联系,他们的所有行动全都指向了纯粹的自己。通过一言一行,人物性格以最凝练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达到了饱满的戏剧张力。 有时候,这只需要一个动作,比如《诺桑觉寺》里凯瑟琳坐在索普马车上的一小段,索普嚷着宣称“上帝保佑!给我五英镑,我可以从这里到约克郡打一个来回,保证一颗钉子不掉”,而凯瑟琳听得目瞪口呆。一个动作,前者的滑稽感,二者的修养的高下便立刻呈现出来。通过戏剧化行动而塑造出的大小人物在奥斯汀小说中数不胜数。 于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看到自私蛮横的爱玛,能感受到措辞浮夸的柯林斯先生的稽态,能看到贪图金钱而在小说前后带着两张嘴脸的蒂尔尼上将,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缩影,奥斯汀没有直接写那个众生百态的时代,而是把他们放在了小格局内通过戏剧效果来最强烈地呈现。为金钱奔波的伪君子,赖婚姻以生存的女性,高尚或卑劣的乡绅……当时那个大千世界的气象就这样在奥斯汀的小格局里勾勒出来。
2009年迷你剧《爱玛》剧照。 所以,奥斯汀的格局虽然小,但不代表她描绘的世界也小,更不代表乏味。她并非一味刻画两三户人家的日常生活,而是在两三户人家搭建的舞台里描绘世界,在角色身上打造不同的人性。即使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小说也因为激荡碰撞的鸣响而异常精彩。阅读时,欣赏的不是故事,而是人,以及角色所代表的人性。 虽然,“可嫁性”总是围绕着她书中的女性,但在“可嫁性”之下呈现的依然是高贵的人性品质,主人公的婚姻自由而不受限制,可以打破门第限制,也可以打破财产差距;可嫁性,这个词在奥斯汀的世界里既是一个世俗的小愿望,也是崇高的理想化归宿。在面对这个理想的时候,尽管从不曾正面论述过什么,但奥斯汀对人间善恶,灵魂高低的把握从不曾倾斜,善恶是非,终有结果。阅读奥斯汀的小说,就像在一个私人的起居室内观望窗外的大世界,拉开灰暗的窗帘,会有遥远的阳光照射进来。 这种明媚的感动,200年来,未曾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