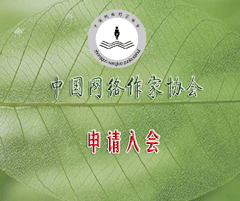|
二.朱氏家族近现代文化代表人物——朱小峰 1986年北京电视台到京郊采风,被当时县乡领导引荐到西永和屯村,因为这个村有个远近闻名的书画社。其发起人之一是朱小峰,当时他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 朱小峰(1899—1989),朱永庆长子,名起予,字小峰,西永和屯朱氏近世家族文化代表人物。朱氏家族传到民国,以朱永庆一脉最为显达,朱小峰从小受家族文化熏陶,兼其家境富裕,因此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比较其父朱永庆,其所涉领域更为广泛,文章之外还涉猎书法、绘画、音乐等等,而尤以书画为精。 因喜欢画画,朱小峰在高小毕业后,于1919年考入由蔡元培倡导成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23年更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受教于陈师曾、王梦白、萧谦中、姚茫父等名师门下,并深受诸师长青睐,尽得他们真传。所学在融会贯通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学习时已小有名气,被同学们赞为“诗书画三绝”,因而还推举他做了班长。1923年,朱小峰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师范系。 毕业后,朱小峰也是首先从事教育业,一边教书一边书画、著作,其书画作品曾在北平、唐山和邢台等地参加过画展,在当时书画界有相当名气。1929年4月12日其发表于《新晨报副刊》的《中国画法之比较谈》,已成为三十年代中国艺术史论中的重要文献。除此还有他的文字创作,其《南行琐记》在刊物上连载,据说当时的稿费就够其长子(朱希曾)读书的学费了。应该说青年时期的朱小峰春风得意。 而且,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他也像其父朱永庆一样开始从政。朱小峰从政的原因,据其后人说有几个方面,一是因为其父朱永庆当时在政界的关系,官官相亲,这些关系主动就会找上门来;二是因为朱小峰当时表现出色,正年轻有为蒸蒸日上……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自己也愿意。 朱小峰的从政经历不是很长,但据说职位升得很快,在河北省邢台县,从政几年就做到了科主任一级,俨然就可以和其父比肩了!但正在这个时候,其父病逝并留下遗嘱,要求后代只做学问不要做官,朱小峰可能因此退出政界,并从此再不提他从政的经历,是以其后人无从了解其从政这段经历的详情。 退出政界重拾教育业。或者是基于家族传统基因,或者是发现自己一直热爱教育,不同于对从政经历的缄默,朱小峰对自己教学经历一直提起。在其离世后,后人在他留下的一本书里发现一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校名!因为平常经常谈起,大家知道那都是其曾经任教过的学校,这页纸就是他从事教育业的总结。 卢沟桥第四中学、潞河中学、富育女中、通县简易师范、乡村师范、通县初师、河北大名第十一中学、河北大名第五女师、泊头镇第九师范、丰台弗伦学校、唐山弗伦学校、石家庄交通大学、北京美术学院……最后是怀柔红螺寺中学。朱小峰任教红螺寺中学,已是解放以后的事,1957年,朱小峰从红螺寺中学辞职,从此离开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这是他继辞官后的又一次重大人生转折。 对朱小峰的从教经历,其后人还是了解一些的,比如任教潞河中学美术教师,那是他从教比较早期的事。在潞河中学任教一年后,他转教富育女中,这一年正是潞河中学第一任中国人校长陈昌佑上任,想要聘他回去潞河教书,双方本已谈妥,但富育女中不放,这件事也就没有办成。那时候教员实行短期聘任,所以朱小峰也就到过很多学校,估计有些学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从教多年,朱小峰任教科目大多是美术、书法、中文、音乐(教钢琴课),具体详情不得而知,其子朱希章只记得他在石家庄交通大学是中文系副教授,在北京美术学院做过庶务处主任,教务襄理等,是中国画讲师,那都是临近解放了。解放后朱小峰被重新安排,最后调到了红螺寺中学教美术。本来这已是固定职业,到了年纪应该可以退休,但因为看不惯时任校长占小便宜贪污几袋白面,朱小峰竟是愤然辞职! 从朱小峰的人生履历不难想象,少年得志中年显达,一路顺风未遇坎坷,这种经历几乎必然造成性格上的某种张扬和偏执。朱希章回忆,父亲年轻时脾气很大,有一次因为其长子朱希曾贪玩误学,父亲一枪从兄长头皮上擦过,吓得他再也不敢贪玩惰学了! 还有就是处理其和著名画家王雪涛的关系。王雪涛(1903-1982),原名庭钧,字晓封,号迟园,河北成安人,原北京画院院长。就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时,王雪涛是其下届师弟,因两人当时都是班长,关系非常密切。一次他们的老师王梦白因与时任校长闹矛盾而罢课,朱小峰和王雪涛共同组织两个年级的学生去跪求,结果王梦白老师哭了,也就恢复了给他们上课。朱小峰与王雪涛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 朱希章记得他小时候两家关系还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去过王家,但后来关系疏远,原因是王雪涛游学日本,与日人交厚。朱小峰痛恨日本人,因此就与王雪涛断绝了关系。他为什么这样痛恨日本人呢?或者因为父亲,或者因为恩师,或二者兼而有之。朱小峰的恩师王梦白死于日本人之手。王梦白是当时绘画名家,经常到日本卖画引起一些日本人嫉妒,后王患痔疮到天津日本陆军医院医治,那些日本人就阴谋治死了他。 王梦白是否死于日本人阴谋没有定论,朱小峰却对此认定不疑,朱希章说父亲痛恨日本人,还有一个因素可能直关自身:恰在王死之前,他随朱小峰到中山公园参观有朱小峰参加的画展。当时遇到一个老头,他看到父亲给这个老头鞠躬,那老头对朱小峰说,你的作品已经成了,只要秋后我们两个合办个画展,你就肯定是名副其实的大家了。朱小峰回来筹备画展,期间却传来王梦白死讯,因此画展没有办成……朱希章后来才知道,那个老头就是父亲的老师王梦白。 “如果画展办成,你爷爷(笔者是朱小峰孙婿)可能就出大名了……”朱希章对笔者说这话时一脸的遗憾。不管因为什么,反正从此朱小峰就恨透了日本人,“恨屋及乌”,因此断绝了与师弟王雪涛的来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小峰性格偏执的一面,后来因为看不惯校长愤然辞职也就不足为怪了。 1957年,58岁的朱小峰辞去公职,回到西永和屯当了农民,没想到从此却遭遇了人生巨大的磨难。西永和屯村绝大部分村民都属于朱氏宗族,朱小峰一脉当时又最显达,被乡里俗称“大门”,其个人成就也受乡里仰慕,加之为人正派,按说回来也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却出在了那个时代。 先是划成分,西永和屯当时400多口人28顷地,人均土地六七亩,朱小峰家9口人32亩地,算是一般户,只是房子多点。朱小峰兄弟四人,分家后其他兄弟相继搬走,房子被他一人赎买,这样一来房子确实太多了,多到让人想要分它。要分房子,朱小峰就必须成为地主,因此他也就被划成了地主。 虽然被划了地主成分,朱小峰回来当时也没多大问题,总是同宗同族,房子分出去也就踏实了。辞职回家的朱小峰,头几年过得还算安稳,耕读诗书画,田园生活固然清苦,安贫乐道也算享受,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朱小峰的生活也就从享受变成了忍受、忍耐,直到无奈。 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岁月,朱小峰的磨难可想而知,地主挨批挨斗自然而然,更残酷的是他再不敢摸他钟爱的毛笔、画笔了……拜过名师的朱小峰,当时已有相当名望,但这些此时就成了罪过。朱希章记得那时家里收藏着父亲诸恩师陈师曾、王梦白、萧谦中、姚茫父的字画……记得还有一张张大千的,这些也成了罪证。真可惜了这些字画!因为恐惧,这些字画都被朱小峰的妻子烧掉了……朱希章说当时家里有两大柜子这样的字画,母亲烧了两天才烧完! 作为地主,挨批挨斗,朱小峰也只能忍受,经历过这些磨难,朱小峰身上再没有了原来的“傲气”,他平静安详,慢慢变成了一个垂暮老人。但让他始终难以忍受的,还是再也不能拿起他心爱的毛笔、画笔……其孙女朱晋晖(笔者妻子)后来回忆,有一个场景一直定格在她的脑子里:一个夕阳西下的背景,爷爷蹲在地上,望着一排树上的小鸟出神,随后又捡起一段树枝,在面前的沙土上划拉,划拉几下抹平,再划,如此再三,最后是蹲在那里久久地发呆…… 好在那样的日子终于结束,“文革”之后,朱小峰又拿起了毛笔、画笔,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快80岁的人了。笔者1981年后见过朱小峰老人,并与之有过几年接触,那是一个非常普通也很慈祥的老人,没事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写诗作画,与之谈论诗词,老人还能思路清晰地对答,再后来就有了西永和屯书画社。 朱小峰一生虽有太多遗憾,但他从教多年,培养了很多弟子,晚年成立书画社,更培养了一些家族子弟和乡邻后辈,让朱氏家族文化得以继续传承。1986年某日,北京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出了《春到牛堡屯》(时西永和屯村隶属牛堡屯乡)文化专题片,电视里的朱小峰老人神采奕奕精神矍铄…… 1989年,朱小峰以90岁高龄安然辞世,他晚年留下的书画被弟子、乡邻广为收藏,但其前期作品大部散佚。朱小峰逝世25年后,其弟子朱起东一次出差河北,经朱小峰早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发现了朱小峰生前的书画作品,在高价求买不得的情况下,将作品拍照,后又多方征集其晚年作品,编辑整理出版了《朱小峰书画集》。这部遗作加之其早年正式发表和出版的《南行琐记》《中国画法之比较谈》《漫画集》等,成为朱小峰留给朱氏家族后人的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