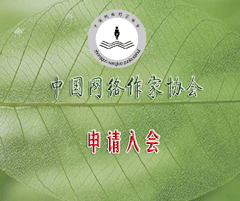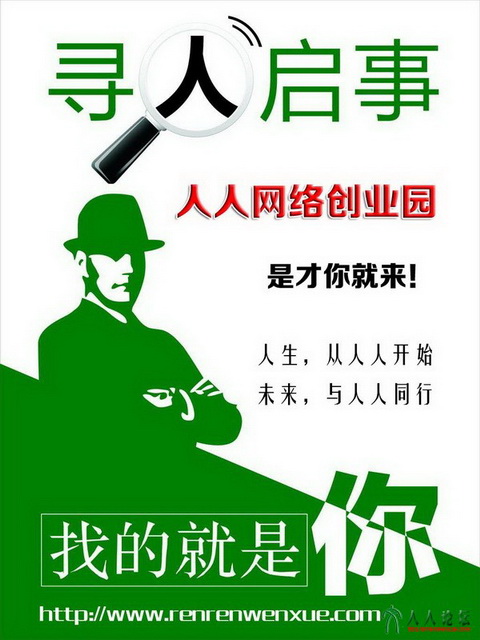|
饮酒,让人欢喜,让人忧 李冬 一 大概没有那种食品像酒一样奇特和有趣了。他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在现实生活中又绝对少它不得。它能给人带来欢乐,也能给人带来烦恼甚至灾难。有人爱它,有人恼它。饮酒,更是说不清楚的话题。我的饮酒经历,就很值得回首一番。 40岁以前,我还不知道酒的魅力,更不知道酒和我的生活以及社会交往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只知道就是辣的。很难入口。那是在生活非常困难的1960年。家里宰了一只小公鸡,顿出的味来好香!肉还没炖熟,我就馋的直咽唾沫了。父亲干活回来了。闻到炖鸡的味道,笑逐颜开,好像见了一个金元宝。摸摸我的脑壳,对我说:“儿子,给我打二两酒去!”当时村里有一个供销社,离我们家老远,去一趟,腿够疼的。可我心疼老爹呀,干活多累呀,去一趟吧。 老爹找到一个扁扁的玻璃瓶子,上面有好多尘土,他用水洗了洗,我就拿着去打酒了。供销社的柜台上,放着棕色的大酒坛子。用酒墩子往外舀。那时的酒,叫白薯干酒,八分一两。我小跑着回到家。鸡肉熟了。父亲咬一口鸡肉,喝一口酒。每饮一口,都要皱皱眉头。发出:“哈,哈”的声音。显出很痛苦的样子。我很奇怪,就问:“辣吗?”父亲说:“怎不辣?吃香的,喝辣的嘛?”我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喝它?”父亲的一句回答,影响了我几十年。他说:“酒,谁喝都是辣的,喝完之后才舒服。” 由此,我就知道,就是辣的,不好喝,就不再碰它了。这自然是最早的诱因。其实,我的生活经历使我没机会接触到酒。社会环境也不容许我能喝到酒。我是农家子弟,家里手头拮据,连我父亲都喝不上酒。村里的老百姓也大多买不起八分一两的白薯干酒。接着,我又上学十几年,不能碰酒。参加工作以后,正赶上“十年动乱”时期。我在农村任教,偶尔,狠狠心进了回饭铺,食客们也大多只是吃一盘素炒饼。我几乎没见过饭铺里,卖过炒菜,更别提有人喝酒了。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了,思想解放了,农村里,赶上红白喜事,有的富裕人家能见到当地产的“二锅头”酒了。由于多年禁锢,饭桌上喝酒的很少,我是滴酒不沾的,没人劝我,我也乐得逍遥。那时,我在饭桌上,从没见过一个醉酒者。如今想来,那时,刚刚经过文革动乱,人人心有余悸,不大痛快。谁能当酒鬼,撒酒疯呢? 又过了五年,在农村盘踞22年的人民公社终于寿终正寝了。没有了生产队,取消了工分,农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里有算计,肯吃苦的庄稼把式渐渐有了余钱。4元多钱一瓶的“通州老窖”有不少人买得起了。那时,不必说过年过节,平时找个由头就要聚之,就要饮之了。就在此时,我也就随波逐流,逐渐进入白酒的饮者之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