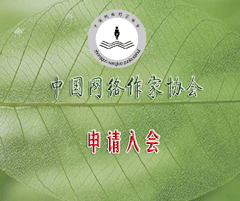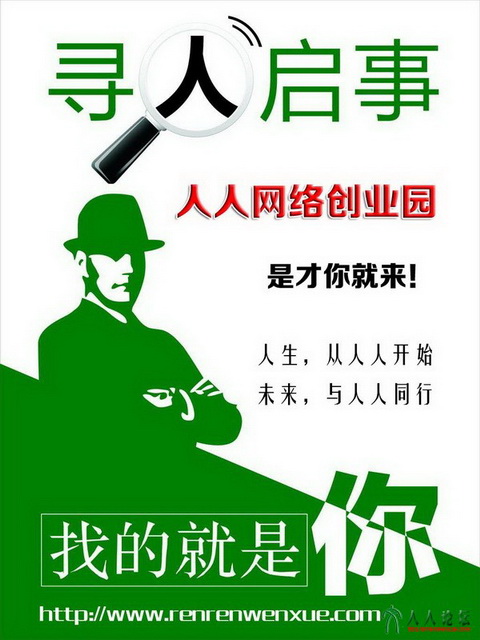|
四 好多时候,饮酒还是悠闲快意的。特别是阔别多年老友相聚,酒盅里似乎饱含着深情厚谊似地。“酒喝厚了,钱耍薄了。”这是俗话,也是实情。“酒逢知己千杯少,好友相聚酒特香。而且很少有人醉卧不醒的情况。 '记得有一次到牛堡屯的“天地和庄园”里饮酒。那天,只是一般的几位同窗好友聚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酒店优雅的环境。如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聚会,这里没有“崇山峻岭”却有“茂林修竹”,没有“清流急湍”,却有奇花异卉。油漆彩画的曲径游廊,连接着一间间幽静的餐室。室内的条幅和国画,多出于通州名家手笔。显得格外亲切。优雅的环境,感化着饮者,一边赏景,一边浅斟慢饮,评诗论文,那叫一个惬意。服务员端上“坂城烧锅酒”来。有人就说出一个典故:“有一次,乾隆皇帝问纪晓岚出个上联:”金木水火土“,让纪晓岚对出下联。没想到,纪晓岚脱口而出:”坂城烧锅酒。“乾隆大喜,赏之。我们几个听万一琢磨。果然很有意思。酒名的五个字。其五个偏旁正好和上联相对,既巧妙,又不俗。我一时高兴,也说了一句上联,那是我们游慕田峪长城时,乘缆车而上,优哉游哉。觉得不如用脚攀登过瘾,就顺口说:“懒人乘缆车,登山游览。”校长一听,大喜,说:“好上脸,谁能对,我请客。”当时就把大伙难住了。我琢磨了几日才有所领悟。此时在这个酒厂说出,如同放了一个礼花弹,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各有想法,又个个犯难,一句话要有三个同音有不同形的字,难矣哉!经过一番讨论和争论,最后确定一句:“工匠造弓箭,围城进攻。”对上一句对联,赢来了一阵欢笑。这次饮酒,喝的好像是“文化饮料”,人生难得到机遇,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赶上节日或纪念日,或以文会友,或师生相聚,饮酒是绝对不可少的。想和他们聊聊了,不说见个面,不说聊聊天,得说聚一聚,喝点儿。和那些或文友或同学的相聚,皆是如此,孟宪良使我的同班学又同桌的学友。那时我们都喜欢都特喜欢诗歌。当代诗人郭小川的《祝酒歌》我们都能背下来:“酗酒作恶的是浪荡鬼,最就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我们社会主义信任这一辈!财主醉了,是因为心黑;衙役醉了,是因为受贿;我们就是醉了,也只是生活的酒啊,太浓,太美!······”我俩分别几年后,他到文化馆画工作,此人比较清高,市场表现出睥睨一切的样子。搞创作,很刻苦,有时干活累了,就叫我陪他喝酒,他喝酒特讲情调,讲氛围。在他家里,餐厅的光线和谐,伴有美妙的音乐。他不爱喝白酒,最爱喝的是金奖白兰地或者青岛生产的威士忌。我也只能顺其自然,顺便尝尝“洋酒”的滋味了。有时,我们也会讨论古人咏酒的诗文,如白居易的《送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俩都觉得这是一首绝妙好诗,是白诗中最佳的一首。仅仅20个字,有时间,有地点,有天气,有心态·····可惜,好景不长,宪良因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同学聚会那天,我斟满一杯酒,洒在地上,算是我对他的祭奠吧。 要是和老楚,刘祥等几个老友聚会,就没有那些讲究了。刘祥做事踏实认真,一边喝酒,却从来不说和酒有关的话,最喜欢谈他的文学理念,说他编辑《运河》杂志的计划。,《运河》这本文学期刊坚持出版十几年了。培育了不少文学爱好者,口碑不错,在北京郊区很有影响。他的心总是专注在办好刊物,培养文学新人的方面,对于饮酒不热衷,也不张扬。他从不打“酒官司”,也不会让酒。其实,他的酒量还是可以的。我能喝酒也和他对饮有关,上个世纪80年代,他下乡时,常到我家喝酒,每次自带白酒一瓶,我俩在不知不觉中,那瓶子就见了底儿。奇怪的是,我们两人从来都没醉过。 老楚是一位很仗义,很有思想又有幽默感的人。就是酒量小,别人喝一口,他只是抿一抿。直到快结束时,他也霍然爽快起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没有一定酒量,就得立马趴下。张溪芜是个红脸汉子,写作勤奋,交游甚广。喝酒也痛快。可惜近几年他总在外地发展,很少见面。近日喝了一回,还是那个饮酒风格,还是那么痛快淋漓。说起张希正,他是我同学中的师哥,在校时就爱好文学写作,很有文才。后来果然当上了文化馆馆长,每次会后,常和我喝酒,他喝的很少,喝几口,脸就涨得红通通的。只是近几年身体欠佳,大概早就戒酒了吧。 总之,文人饮酒,讲究气度、气氛。无论怎么喝,不离文学。也从没有过争吵或有人大醉的情景。文人饮酒,最能体现“酒文化”的色彩,不亦快哉! |